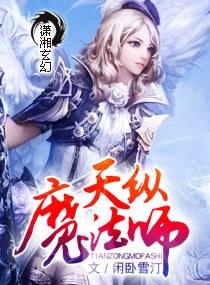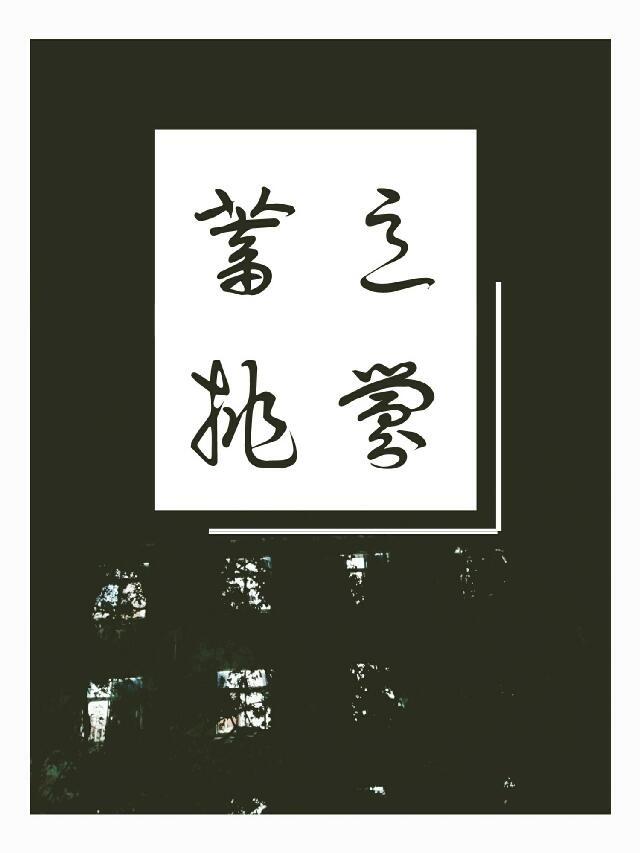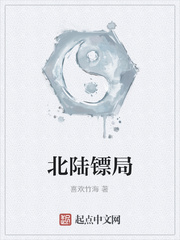塵煙舊夢
九月中旬,秋意漸濃,明川的清晨薄霧蒙蒙,天色還未亮透。
葉望在鏡子前迅速地整理好自己的風衣,提上包出了門。
昨天,明川北郊在建的地鐵工程挖出了一座大崟時期的王陵,考古隊昨晚就已經入駐施工現場進行勘驗。
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,葉望一行人終于到達了發現陵墓的施工現場。但四周都被警戒線圍了起來,很難看清裏面的景象。
一個年輕男人迎了上來:“您好,我是考古隊的工作人員,請問幾位是?”
“您好,我是明川電視臺《明川夢影》節目組的編導葉望。”葉望把名片遞給對方,“我們昨天和明川考古研究所的吳主任聯系過了,想來采一些這次考古的素材,做一期紀錄片,吳主任讓我們今天過來找你們的領隊。”
對方看了看名片:“好的,請跟我來吧。”
男人将葉望一行人帶到考古隊的休息處:“幾位請坐,我去叫我們領隊。”
過了片刻,葉望聽見一陣腳步聲傳來,她緩緩側身,模糊看見一個颀長的身影向她走來。她近視四百多度,卻不喜歡戴眼鏡,只能隐約看見這個男人穿了一身黑色的寬松工裝。男人越走越近,輪廓逐漸在她眼前清晰起來,她倏地對上了那雙鏡片後的深眸。男人約莫三十歲出頭的樣子,臉型瘦窄,眉眼深邃,鼻梁高挺,可能是剛從挖掘現場出來,黑色的工裝上沾滿了泥土。
男人剛洗過手,拿起旁邊的紙巾擦了擦手上的水漬:“葉編導你好,我是考古隊的領隊,景策。”他把擦過手的紙丢進垃圾桶,有些不好意思:“這手摸過死人的東西,不吉利,就不和各位握手了。”
葉望伸出手,打趣說道:“景老師說的哪裏話,大家從小就學唯物主義,誰還信這些?”
景策笑了笑,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,遲疑了幾秒後輕輕回握了葉望的手。她指尖冰涼的觸感傳到景策手上,景策臉上的表情突然之間似是凝固了一般,望着她的手出了神。她卻沒有發現景策臉上的異常,只是自然地抽出被景策握住的手指,景策也立刻回過神來。
葉望很快就和景策溝通好了拍攝的相關事宜,景策帶着葉望和節目組的工作人員來到出土現場。黃色的泥土之下,隐約露出一些建築物的輪廓。
“景老師知道這是誰的墓嗎?”葉望随口問了一句。
“北祁王。”景策答道。
“北祁王?”
“在大崟,這種墓室規格只有王侯可以使用,看到那座碑了嗎?”
葉望順着景策指的方向看去,只見黃泥中露出一角花紋精美的青色石頭。
“是那塊石頭嗎?”
景策搖頭:“那不是石頭,那是烏山玉,按大崟的禮制,只有皇室可以用烏山玉制作墓碑。所以這墓的主人不是普通的王侯,而是有皇室血統的親王。”
葉望仔細回憶之前看過的資料:“明川在歷史上叫作祁州,祁州在大崟時期隸屬北陸……”
“對。”景策順着她的話說,“大崟時期,鎮守北陸的王侯中只有北祁王族姓蕭,和皇室有親緣關系,所以這墓室的主人必然是北祁王。”
“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,歷史上有三代北祁王,老北祁王是天武皇帝的親弟弟蕭钺,蕭钺的長子蕭昀繼承了父親的王位,是第二代北祁王,第三代北祁王則是蕭昀的次子蕭策。那這座墓室的主人是哪一個北祁王呢?”
“葉編導歷史學得不錯。”景策笑了笑,“等墓碑全貌出土,就可以根據上面的碑文判斷是哪一位北祁王了。不過這陵墓規模龐大,裏面也許不止一位北祁王,有可能整個北祁王族都被葬在此處。”
“哎我突然發現,小北祁王的名字和景老師的名字都有一個‘策’字!”攝像師老于突然插了一句,“以前上歷史課的時候老師說過,這小北祁王戰功赫赫,有戰神降世的美譽,景老師的父母不會是因為仰慕蕭策才給景老師取這個名字吧?”
景策唇角微揚,輕輕搖頭:“借光景以往來兮,施黃棘之枉策。這才是我的名字。”
天啓四十八年春,北陸祁州城。
沉重的城門被緩緩拉開,門外烏壓壓的軍隊如密密層層的烏雲一般綿延到遠處。春寒料峭,涼風襲人,軍旗獵獵。
軍隊最前方的男人一身黑甲,神色凜然,瘦削的臉頰上落了一道傷口,殷紅的血色滲出了皮膚,興許是在戰場上受的傷。男人拉起缰繩,震聲呼道:“北祁王軍聽令!随我入城!”
城樓之上,號角連天,雄渾壯闊。
滿城百姓齊齊跪拜,對領軍的男人行禮:“恭迎世子凱旋!恭迎世子凱旋!”
北祁王府門前,白發蒼蒼的蕭昀身姿挺拔,一身黑袍襯得他精神矍铄,似是可以看見他年輕時的英姿。
“王爺,天氣尚未回暖,還是回堂中等世子吧。”一個老仆上前說。
“不必,阿策應該快到了。”
話音正落,一陣馬蹄聲便向這邊逼近。領軍的男人飛身下馬,快步上前跪在蕭昀面前:“父王,路途遙遠,兒來遲了。”
蕭昀連忙将男人扶起:“不遲,吾兒平安歸來便好。”
蕭昀注意到兒子臉上的刀傷,喚來身後的老仆:“順謙,快去把孫醫士叫來,給世子治傷。”
北祁王府,敬松堂內。
孫醫士熟練地為蕭策包好傷口,轉身對北祁王說:“王爺,世子吉人天相,都是皮外傷,按時換藥,七日可愈。”
“有勞孫醫士。”蕭策重新穿好衣裳。
“世子客氣了。”孫醫士收拾好處理傷口的工具,揖手道:“孫某告退。”
見孫醫士離開敬松堂,蕭昀将一份邸報遞給蕭策,低聲說:“這是前日晏京傳來的邸報,你看看。”
蕭策展開邸報,大致翻閱了片刻:“朝中官員變動竟如此巨大,難道……”
蕭策暗自思忖,朝中官員調度變動再正常不過,但按常理來說不會一次就出現大規模的官員調動,否則可能引起朝野震動,可這邸報上所言,竟有半數的重臣有了調動。
他忽然警覺地擡眸,只見父親輕聲嘆氣,微微點頭道:“是的,應是要變天了。”
蕭策素來不關心朝政,暫時想不到父親所言的“變天”會是什麽個變法,安慰父親:“父王不必憂心,自我大崟開國,祖父便帶着家眷北上,我北祁王族已立誓世代鎮守北陸。只要守好這北陸,那晏京的天是晴是雨,風都吹不到祁州。”
“但為父近日心中總有不适,時常胸悶氣短,為父擔心……”
“父王必是憂心兒子在外征戰,恐兒身陷危機,憂慮過度。如今兒已平安歸來,父王就不必多慮了。”蕭策一面安慰蕭昀,一面繼續仔細翻閱邸報,他的目光停在一個名字上:“大理寺少卿公儀景?公儀叔父早在十四年前就已經去世,我記得公儀家的子弟在十四年前也盡數遇難,這公儀景又是何人?”
“是,公儀家一個兒郎也沒有留下,這公儀景,是公儀嵩唯一的女兒,當年僥幸逃過一劫。公儀家遇難後,她被長公主收留,後又師從刑部尚書裴鑒英。裴尚書年事已高,辭官休養,致仕前向陛下舉薦了公儀景。這丫頭竟從大理寺的一個寺正一路做到了大理寺少卿,倒也繼承了些公儀嵩的才能。”
“竟是個女兒。”蕭策有些訝異。
晏京,大理寺。
“臣接旨,謝吾皇隆恩。”公儀景從劉公公手中接過敕旨,叩謝道。
“恭賀公儀大人升任大理寺少卿。”劉公公笑臉盈盈。
“有勞劉公公。”公儀景客氣地回道。
“那老奴便告退了,不煩擾大人公事。”
公儀景笑着微微颔首:“元青,送劉公公。”
身後的少年上前兩步:“是。”
公儀景看着元青帶着劉公公遠去,握緊了手中的聖旨。
“如今大人升任大理寺少卿,為何大人看起來卻并不開心。”子淳問道。
“沒有不開心,不論身居何職,都是在其位謀其事,把公務處理妥帖才對得起這身官服。”公儀景草草敷衍兩句,轉身回了屋。
不一會兒,子淳來報:“大人,老尚書派人來送信,邀大人今晚去用家宴。”
公儀景放下手中的公文:“好。”
今日公務不多,公儀景審完卷宗便離開大理寺,來到了裴府。
家宴不算熱鬧,草草用完膳後,裴鑒英屏退了其他人。
“師父可是有話對弟子說?”公儀景心知肚明。
“阿景可知何人舉薦你升任大理寺少卿?”
“這,難道不是陛下的意思?”
“莫說大理寺,就算是放眼整個朝堂,都找不出第二個為官的女子。當年陛下恩準你任大理寺寺正,已是破了先例,如今将你升任大理寺少卿,官居要職,又怎會是陛下的意思?”裴鑒英抿了口茶,神色凝重。
“師父的意思是?”
“自李博調任寧州,大理寺少卿之位空缺已久,陛下也沒有合适的人選。你天資聰慧,才能過人,但你終究是個女兒,陛下不可能主動将你調至這般要職。必是有人在陛下面前力薦,陛下才提拔你。”
“這舉薦之人,恐怕不安好心吧?”公儀景恍然大悟,“自我入大理寺,朝中衆臣便頗有微詞,議論紛紛,說些女人為官不成體統的話。此人卻偏偏舉薦我做大理寺少卿,看似是提拔了我,實際上是想讓我離那些卷宗遠一點吧。”
裴鑒英點頭:“正是。當初為師舉薦你任寺正,正是因為寺正可以直接審理案件,查閱卷宗,這樣你便有機會尋到你父母遇害的線索。如今,你升任大理寺少卿,須處理重大案件,那些卷宗,你恐怕不好再拿到了。”
“看來,這舉薦之人,就是害死我父母的真兇。”公儀景有些哽咽。
裴鑒英點頭:“他已經坐不住了。你一查到郭瑕身上,他便有了行動,這說明你離真相很近了。”
“可這郭瑕至今不肯招,弟子現在想親審郭瑕,已經難了。”
裴鑒英放下手中的茶杯,緩緩擡頭,眼前的女郎身着男子樣式的翻領長袍,清瘦的身材裹在寬大的衣衫裏,如一枝新抽的嫩竹。
他還記得二十多年前,公儀嵩抱着剛足月的小嬰兒,欣喜若狂地對他說:“義兄快看,這是我的阿景,我唯一的女兒。”
他往那襁褓中望去,一個粉雕玉琢的嬰孩正撲騰着小小的雙手,一雙眸子水靈閃爍。他輕輕握住小嬰孩的手,那粉嫩的手指柔如春芽,他生怕弄疼了她,輕聲對這嬰孩說:“阿景,我是你的義伯。”話音剛落,那小嬰孩便叽叽呀呀地笑了。
後來這小嬰孩慢慢長大,成天蹦蹦跳跳,到處闖禍,又是爬樹掏鳥窩又是下河摸魚,絲毫沒有名門閨秀之風。但公儀嵩卻說:“我們阿景不需要做名門閨秀,想幹什麽就幹什麽。”
小阿景在公儀嵩的庇護下被養得活潑可愛,可那個天真爛漫的小女郎卻在十四年前的變故中痛失雙親,自此之後,她像是一夜之間少年老成,再也沒有如兒時那般快活過。
裴鑒英忽然有些傷神:“阿景,為師是不是做錯了?”
“師父何錯之有?”公儀景不解。
“為師當初或許不該舉薦你,不該看着你步入朝堂。”裴鑒英輕嘆,“阿景可曾後悔?”
“為何後悔?”
“若不為官,阿景如今應該已經覓得良人,有所依靠,不必像如今這般步步為營,如履薄冰。你十六歲便進了大理寺,如今六年過去,你也錯過了嫁人的好年紀。更可怕的是,這條路不知還有多少危險等着你,若稍有不慎,你恐怕就會和你父母泉下相見,阿景不後悔嗎?”
“阿景不曾後悔。”公儀景上前,坐得離裴鑒英更近一些,“師父,這是我自己的選擇,是我自己要入朝為官。我知此路艱辛,但阿景從未後悔。自阿爹阿娘和兩個兄長去世,是師父日複一日地耐心教導我,教我讀書識字、學習政務。從前阿景年幼,為公儀家報仇之責一直是師父在承擔,但如今阿景已經長大了,師父能做到的,阿景也一定可以做到。”
裴鑒英已經六十二歲了,雙目也漸漸渾濁,不似年輕時那般清明,但他仍努力看清眼前女郎的模樣。良久,他慈愛地輕撫公儀景的頭發,眼眶濕潤地緩緩說道:“阿景,你和你父親,長得很像。”